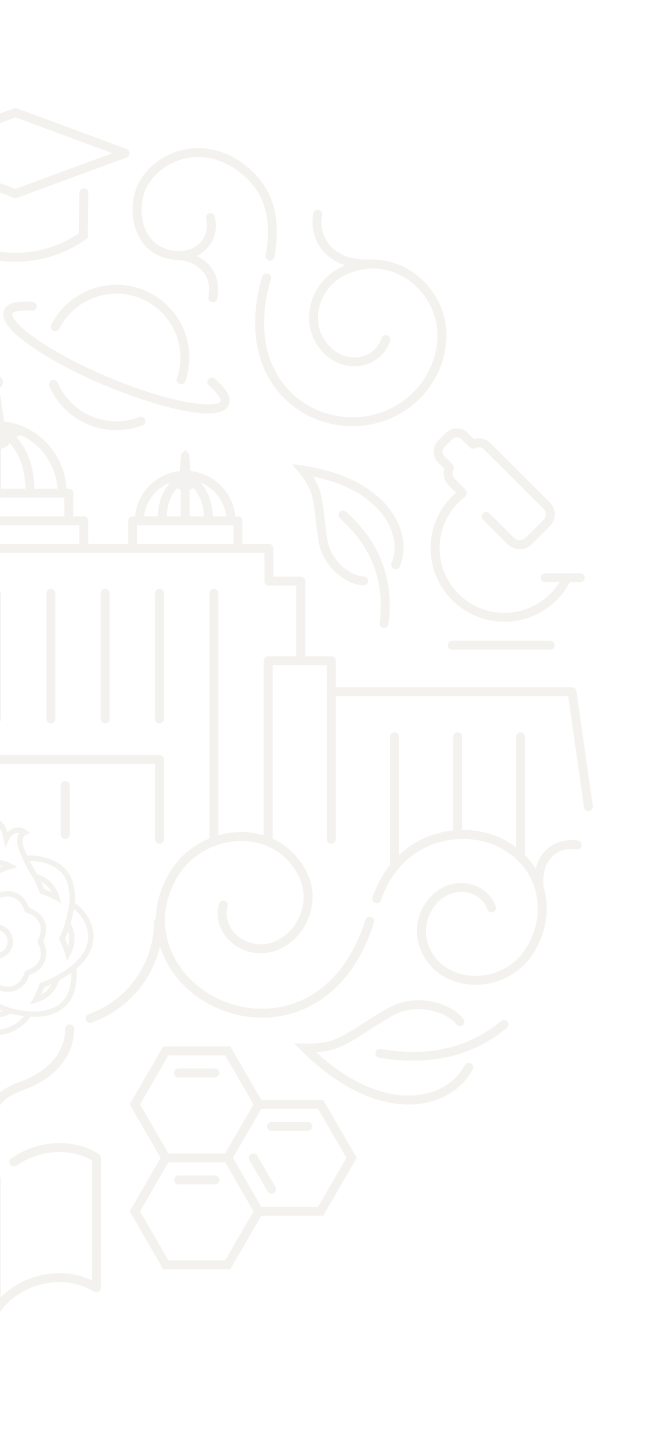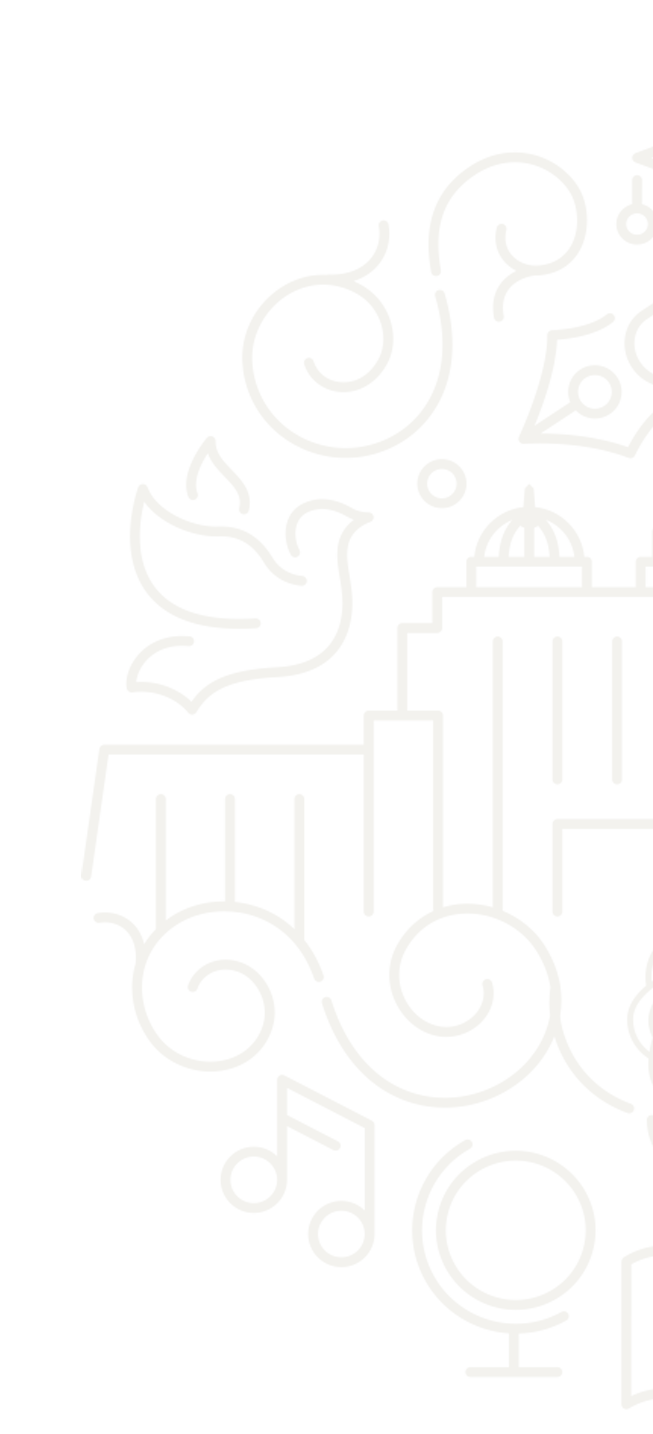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草原生态保护研究主要分析沙漠化发生原因及其对策,认为乱开垦、乱开发、人口激增等人为因素是生态破坏的主要根源。并对承包责任制或草畜平衡政策的详细指标体系提出疑问,基于“公地的悲剧”理论和产权理论,提出草原内外管理的强化,或者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角度研究,指出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博弈对草原生态环境的深刻影响等。尤其是,2010年以后草原畜牧业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研究成为主流,这些研究认为草原生态的劣化主要取决于世界大气候变化,在极端天气接连不断的状态下,草原畜牧业如何适应环境变化成为重点,尤其牧户主动采取的增收、环保行为受到重视。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蒙古国经济研究进入全维度、更深度、高层次阶段。已有研究发现,内蒙古草原畜牧业和蒙古国草原畜牧业之间存在轮换使用草牧场和适度放牧的共性需求。因此,传统产业、发展历程、基础草场、经营者牧户民族属性等众多相似性,引发了更多的中蒙国际比较分析。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赤峰考察工作时强调,建设祖国北方和首都生态安全屏障是战略性的任务,是我们要世世代代做下去的事情。因而,生态保护是内蒙古乃至中国北方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必然途径,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本项目主要研究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中蒙两国草场生态保护中牧户经营的作用与可持续性比较研究。其一,研究牧户现在的创收经济行为是否可持续。主要分析经济行为和生态环境的共存机制和“生态功能”无法发挥作用时的牧户退出机制。具体内容包括在中国北方牧区生态移民和蒙古国牧区“游牧”行为的比较分析中,判明不同地区“同一种转移行为”在不同决策(政策性、自愿性)下产生的经济效应和生态效应。最终确定在草原畜牧业牧户持续经营或退出的选择中牧户决策比较合理的模式,也就是明确牧户经营与草场保护发生冲突时,自生性保护草原机制和政策性保护草原的“分界点”。其二,牧民传统文化、经验积累等对生态保护的作用。传统文化等非货币价值体现在牧户自我保护草场行为中,成为生态价值评估的主要内容。该子课题主要分析生态环境保护中牧民自律性行为的价值和作用。其三,明确牧户内生性生态保护机制与政策等外延性动力之间的平衡关系。生态补贴政策长时间扶持生态保护的可能性并不大,也不能投入大量资金来支持草原畜牧业,因此,国家生态政策支持过程中,牧户生态保护如何发挥最大化作用是关键问题。
第二部分,中蒙两国生态保护合作中牧户对生态保护作用的比较研究。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共同建设中,草原畜牧业经营以“草地、牲畜、牧民”三要素有机结合为基础,两国草原畜牧业完全表现出非偶然的共性。其一,牧户生态保护作用的激励机制研究。包括以下内容:在不同政策背景下,各国政府如何鼓励牧户自主性生态保护行为,而并非用政策来替代;分析如果我国北方牧区大幅度减少生态补贴,牧户承担较为艰巨任务时牧区能够维持下去的生态保护行为与蒙古国、俄罗斯牧区牧户草场保护行为的区别和获取激励措施的合理理由;探究假设蒙古国经济有所好转,生态保护投入大幅度增加时,鼓励发挥牧户作用的合理性如何确定等。其二,探讨基于生态经济规律的草原畜牧业现代化发展模式。利用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生态效应等三方面的有效变量,分析如何提高牧户收入,让牧户在更宽敞的经济空间内决策生态保护行为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提高两国牧区牧户经营的自我发展能力及其畜牧业与草地生态协调能力的确认和建设等。从而论证经济与生态共存体系才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牧户保护生态是根本的观点。在政治与战略性合作环境积极敞开的条件下,两国草原畜牧业经营牧户对生态保护作用研究,可以明确生态保护中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差异,同时,阐释了在气候、地势地貌极度相似的状态下,牧户经营内生性生态保护措施的动机和机制。最终确定牧户对生态保护的作用,建立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并适合草原生态环境的一般性模型,供各国政府作为生态政策的理论依据。